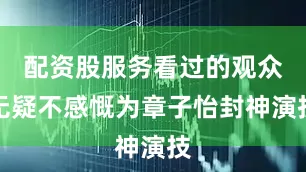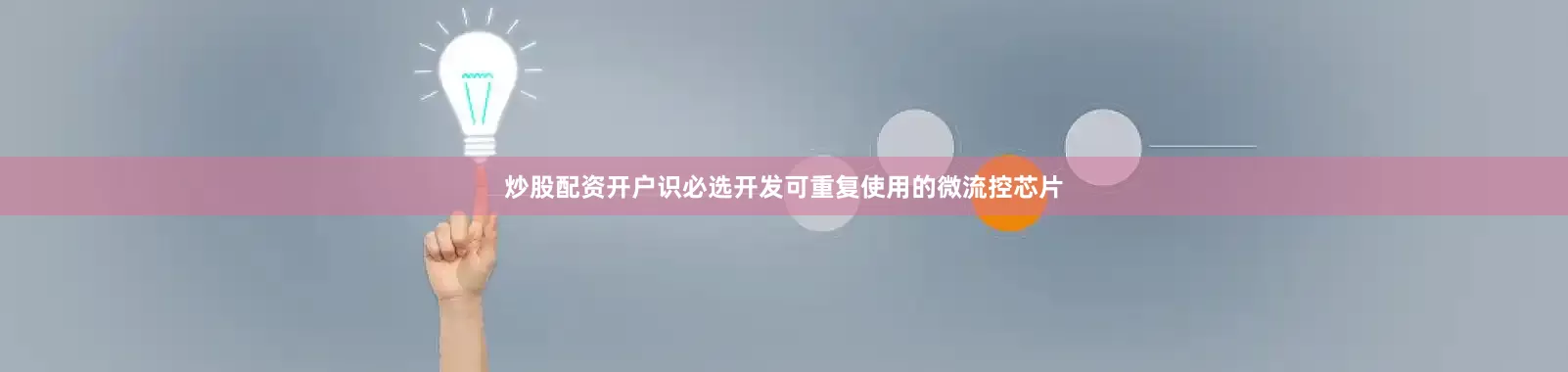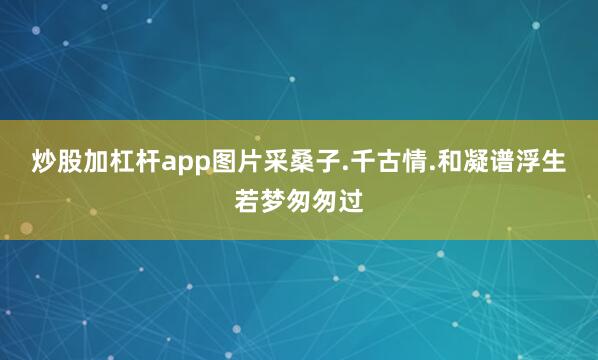在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市,一座名为“20世纪广场”的公共空间内,矗立起了一尊毛泽东的雕像。这尊雕像所展现的,既非晚年那不怒自威的威严,亦非中年时期那紧锁的眉宇,而是伟人风华正茂的独特风采。
毛泽东时代未逝。
在法国,活跃着一群对毛泽东充满狂热的“职业粉丝”。这番景象,曾令不少在法的华人既感慨又赞叹。
1968年,法国见证了“五月风暴”的爆发。这场风暴自巴黎大学蔓延开来,众多学生集会,抗议当局对反越战学生的逮捕。随着政府采取愈发铁血的镇压手段,抗议的队伍不断壮大,直至最终,几乎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纷纷加入了这场游行示威的行列。

“回望上世纪60年代,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犹如一种独特的‘吸引力’,我与我的同龄人,正是在深入研读其专著、领悟其思想的过程中,孕育出了强烈的改变世界的决心。”
往昔,他们常被冠以“忧虑的一代”或“未成熟的一代”之名,更有社会学者以“热衷罢课游行、与警方对峙、占据校园的热血青年”来形容他们。未来是渺茫的。”
最终,热拉尔·米勒所选择的武器是心理学,而与他同龄的人,有的成为了医生、律师、哲学教授、慈善家……“我们那一辈的青年学子,在先生的引领下,无不学有所成。”
他们是左翼无产阶级运动的杰出领袖,包括阿兰·热斯马尔、霍朗德·卡斯托,《解放报》的资深主编塞尔日·朱利,以及社会活动家贝尔纳·德博尔等,均为社会各界所瞩目。

这种抗争暴政、抵御强权、抵抗侵略和压迫的不屈精神,曾在“五月风暴”期间激荡着学生们的呼声,至今依然深深触动着成为父母和祖父母的法国民众。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尊敬与领悟,将通过一代代口耳相传,传递至子孙后代。
事实上,尽管有些人未曾深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,他们依旧对他充满敬仰,“众所周知,这位伟人曾引领我国崛起,面对外来压力从不低头,堪称真正的强者。而且,他对法国的深入了解也为人称道,不是吗?”
马纳克,这位曾身居法国驻华大使要职的官员,在回忆中提及:“毛泽东对法国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,尤其是对法国革命以及巴黎公社,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。他视法国革命为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运动,其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篇章。”
“曾有一次,主席欲阅读《拿破仑传》,挑选了数本译本,与他同读的同志未能尽数翻完,而主席却已将三册尽阅。”

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之际,毛泽东显得十分好奇,询问道:“拿破仑之死,究竟是由何疾病导致?传闻中说法各异,究竟是胃溃疡,还是胃癌呢?”
德姆维尔说:“可能是胃癌。”
毛泽东轻声自语:“他不是在遗言中提到要解剖吗?当时医生也没弄明白。”见德姆维尔露出微笑,毛泽东便转换了话题:“我觉得拿破仑对我们的影响颇深,法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你知道吗,《国际歌》源自你们的国家,而且,你可能不会相信,我还会唱你们的《马赛曲》呢!”
在法国:树立毛像
约尔格·伊门道夫是著名的雕塑家和画家,他被后来者称之为“活着的大师”,可他却以“毛派艺术家”自居,他说:“毛泽东先生是我的偶像。人这一生,如果一定要崇拜一位政治家,我定要大声说出他的名字。
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主席的离世之讯,经约尔格·伊门道夫通过多源途径核实无误。在那个悲痛的日子里,他重温了《矛盾论》的篇章,并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内主持了一场肃穆的追悼仪式。
“他,我们的引路人,正是通过研读他的著作,我得以加入“团结”组织,进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并主动投身于对中国的深入了解。”
直至1988年,约尔格·伊门道夫携其杰作,踏海越洋抵达我国。他的旅程,唯一的落脚点,便是毛主席纪念堂。在那里,他久久地凝视着毛主席的遗体,离去时,他深深地鞠了一躬,话语中充满了感激:“感谢您,让我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渺小。”

2012年7月24日,幕布缓缓落下,一尊栩栩如生的毛泽东塑像在蒙彼利埃的“20世纪广场”之上静默矗立。他身着戎装,右手高举,目光永远凝视着远方。
昔日,此广场便矗立着列宁、戴高乐、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、丘吉尔、饶勒斯五位伟人的雕像。与毛泽东同志的塑像同期入驻的,还有曼德拉、梅厄夫人、甘地、纳赛尔等杰出人物的塑像,每尊雕像皆高达三米。
此项目堪称蒙彼利埃已故市长弗雷舍的“未竟之志”。社会党人让·皮埃尔·穆雷表示,“前任市长的初衷,不过是希望这些塑像能够象征着20世纪那些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,成为历史的见证。”
显而易见,这是对诋毁雕塑家政治立场的恶意行径的严厉谴责。在24日的揭幕典礼上,极右翼势力纠集了一批人,意图对新塑雕像进行破坏。让·皮埃尔·穆雷无奈地摇了摇头,说道:“尽管他们把这所谓的‘小动作’拍下并上传网络,幸运的是,并未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。”

即便是大多数市民,也对在广场树立塑像的做法表示出理解,他们表示:“实际上,这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一种敬意,而非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崇拜,因此我们不应对此反应过于激烈。”
饶是如此,蒙彼利埃政府依然难逃被打为“毛派粉丝”的“嫌疑”。为了平息争议,也为了让市民更加了解伟人,蒙彼利埃政府继续在广场建了一个“生平事迹介绍亭”。
政府阐述称:“与其仅是拆除塑像,不如引导公众深入理解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,与之对话,进而亲近历史。”所有历史事件的叙述均由资深历史学家亲笔撰写,“我们力求做到公正无偏,客观呈现。”
“中国,亦世界”
“因为是他,重新赋予了中国的尊严。”
约尔格·伊门道夫曾言:“毛泽东不仅仅属于中国,他更属于全世界。”
实际上,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并未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。
五四运动期间,众多青年才俊纷纷踏上赴法留学的征途,而他却选择逆向而行,扎根国内,潜心钻研中国之国情。他坚定地表示:“我此刻宁愿成为那位倡导留学国内政策的人。”
此后,他精心规划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蓝图,彼时,他的目标依然明确:“我们的求学宗旨,旨在变革社会,所追求的,正是实现这一宗旨所需的知识与智慧。”
他潜心研读卢梭、孟德斯鸠的著作,却并未对西洋文化顶礼膜拜。在那个中国弥漫着浓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的时代,毛泽东曾多次向留洋学子叮嘱:“务必先精通国学之精髓,然后再赴海外寻求西方学问的精要。”如此,归来之后方能继续寻求拯救国家和人民的途径。
某人士质问:“仁兄辩才无碍,论理透彻,为何却不跨出国门,亲自去探究一番?”

他微微一笑,说道:“我们应当派遣一些人走出国门,去领略异国的新奇,汲取其中的新知,深入研究有价值的学问,再将所学带回国内,以革新我们的国家。至于我自身,所掌握的知识有限,若是能将更多的时间倾注于国内事务,无疑将对我国的发展更有裨益。”
自新中国成立之后,他愈发繁忙,既要关注国内,亦需关照国际。1964年,我国与法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常化,这一事件无疑标志着中法两国关系的冰封得以彻底打破。
戴高乐适时发表感慨:“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,亲自与那传说中的毛泽东一晤。”
然而,戴高乐未能亲自目睹这一夙愿成真,便在1970年11月不幸骤然离世。直至1973年9月,其继任者蓬皮杜总统方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,成为西欧国家首位在任国家元首的访华之举。
在此次访华期间,蓬皮杜几乎享尽了无上的尊崇:周恩来总理与邓小平同志亲自莅临机场迎接,随后,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故宫;毛主席亦在中南海的私人住所中,亲自接待了蓬皮杜。
“周恩来在我所结识的众多领导人中,是最具风度的一位;而毛泽东则是我见过的最豪迈、最幽默、最睿智的领导者。我将这一切归功于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。”

1974年,德斯坦先生即将就任法国总统之际,一位来自非洲某小国的国家领导人莅临我国进行友好访问。
“下一任法国总统是谁?”
“自是吉斯卡尔·德斯坦先生无疑。”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应。
此刻,德斯坦尚是一介名不见经传的青年,未能获得任何主流媒体的支持与青睐。
两年之后,他出席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毛泽东同志的追思活动。作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,他更是独一无二的,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外国使馆。
比较好的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